拟古九首
荣荣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。
初与君别时,不谓行当久。
出门万里客,中道逢嘉友。
未言心相醉,不在接杯酒。
兰枯柳亦衰,遂令此言负。
多谢诸少年,相知不忠厚。
意气倾人命,离隔复何有?
辞家夙严驾,当往至无终。
问君今何行?非商复非戎。
闻有田子泰,节义为士雄。
斯人久已死,乡里习其风。
生有高世名,既没传无穷。
不学狂驰子,直在百年中。
仲春遘时雨,始雷发东隅。
众蛰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
翩翩新来燕,双双入我庐。
先巢故尚在,相将还旧居。
自从分别来,门庭日荒芜;
我心固匪石,君情定何如?
迢迢百尺楼,分明望四荒,
暮作归云宅,朝为飞鸟堂。
山河满目中,平原独茫茫。
古时功名士,慷慨争此场。
一旦百岁後,相与还北邙。
松柏为人伐,高坟互低昂。
颓基无遗主,游魂在何方!
荣华诚足贵,亦复可怜伤。
东方有一士,被服常不完;
三旬九遇食,十年著一冠。
辛勤无此比,常有好容颜。
我欲观其人,晨去越河关。
青松夹路生,白云宿檐端。
知我故来意,取琴为我弹。
上弦惊别鹤,下弦操孤鸾。
愿留就君住,从令至岁寒。
苍苍谷中树,冬夏常如兹;
年年见霜雪,谁谓不知时。
厌闻世上语,结友到临淄。
稷下多谈士,指彼决吾疑。
装束既有日,已与家人辞。
行行停出门,还坐更自思。
不怨道里长,但畏人我欺。
万一不合意,永为世笑嗤。
伊怀难具道,为君作此诗。
日暮天无云,春风扇微和。
佳人美清夜,达曙酣且歌。
歌竟长叹息,持此感人多。
皎皎云间月,灼灼叶中华。
岂无一时好,不久当如何。
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
谁言行游近?张掖至幽州。
饥食首阳薇,渴饮易水流。
不见相知人,惟见古时丘。
路边两高坟,伯牙与庄周。
此士难再得,吾行欲何求!
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
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
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
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!
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。
荣荣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。
茂盛幽兰在窗下,依依垂柳在堂前。
初与君别时,不谓行当久。
当初与你告别时,未讲此行很久远。
出门万里客,中道逢嘉友。
出门万里客他乡,半道交朋结新欢。
未言心相醉,不在接杯酒。
一见倾心似迷醉,未曾饮酒尽言谈。
兰枯柳亦衰,遂令此言负。
幽兰枯萎垂柳衰,背信之人违誓言。
多谢诸少年,相知不忠厚。
告诫世间青少年,相知未必心不变。
意气倾人命,离隔复何有?
你为情谊愿献身,他将你弃无情感。
辞家夙严驾,当往至无终。
辞家早起备车马,准备远行去无终。
问君今何行?非商复非戎。
请问前行欲何为?不经商也不当兵。
闻有田子泰,节义为士雄。
听说有位田子泰,节义崇高称豪英。
斯人久已死,乡里习其风。
虽然此人久已死,乡里承袭其遗风。
生有高世名,既没传无穷。
在世之时名誉高,死后美名传无穷。
不学狂驰子,直在百年中。
不学奔走逐名利,荣耀只在一生中。
仲春遘时雨,始雷发东隅。
二月喜逢春时雨,春雪阵阵发东边。
众蛰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
冬眠动物皆惊醒,草木润泽得舒展。
翩翩新来燕,双双入我庐。
轻快飞翔春燕归,双双入我屋里边。
先巢故尚在,相将还旧居。
故巢依旧还存在,相伴相随把家还。
自从分别来,门庭日荒芜;
你我自从分别来,门庭日渐荒草蔓。
我心固匪石,君情定何如?
我心坚定不改变,君意未知将何如?
迢迢百尺楼,分明望四荒,
登上高高百尺楼,清晰可见远四方。
暮作归云宅,朝为飞鸟堂。
夜间云聚栖其内,白日鸟集作厅堂。
山河满目中,平原独茫茫。
远处山河尽在目,平原一片渺茫茫。
古时功名士,慷慨争此场。
古时热恋功名者,慷慨争逐在此场。
一旦百岁後,相与还北邙。
一旦丧身离人世,结局一样葬北邙。
松柏为人伐,高坟互低昂。
墓边松柏被人伐,坟墓高低甚凄凉。
颓基无遗主,游魂在何方!
无主墓基已毁坏,谁知魂魄在何方?
荣华诚足贵,亦复可怜伤。
生前名利实可贵,如此凄凉堪悲伤!
东方有一士,被服常不完;
东方有位隐居士,身上衣服常破烂。
三旬九遇食,十年著一冠。
一月才吃九顿饭,十年总戴一顶冠。
辛勤无此比,常有好容颜。
辛勤劳苦无人比,和悦面容乐贫寒。
我欲观其人,晨去越河关。
我欲前行访问他,清晨出户越河关。
青松夹路生,白云宿檐端。
青松生长路两边,缭绕白云在檐间。
知我故来意,取琴为我弹。
知我特地前来意,取琴为我来轻弹。
上弦惊别鹤,下弦操孤鸾。
先弹凄怨别鹤操,又奏高洁曲孤鸾。
愿留就君住,从令至岁寒。
我愿长留伴君住,从今直到岁暮寒。
苍苍谷中树,冬夏常如兹;
葱郁苍青山谷树,冬天夏日常如此。
年年见霜雪,谁谓不知时。
年年经历霜和雪,更变四时岂不知?
厌闻世上语,结友到临淄。
已厌听闻世上语,交结新友去临淄。
稷下多谈士,指彼决吾疑。
齐国稷下多谈士,指望他们解我疑。
装束既有日,已与家人辞。
备好行装已数日,且同家属告别离。
行行停出门,还坐更自思。
欲行又止心犹豫,还坐重新再三思。
不怨道里长,但畏人我欺。
不怕此行道路远,担心谈士会相欺。
万一不合意,永为世笑嗤。
万一相互不合意,永远为人所笑嗤。
伊怀难具道,为君作此诗。
心内之情难尽诉,为君写下这歌诗。
日暮天无云,春风扇微和。
日暮长天无纤云,春风微送气温和。
佳人美清夜,达曙酣且歌。
佳人喜爱清澄夜,到晓酒酣欢唱歌。
歌竟长叹息,持此感人多。
歌罢凄然长叹息,此情此景感伤多。
皎皎云间月,灼灼叶中华。
皎洁明月在云间,绿叶之中鲜艳花。
岂无一时好,不久当如何。
虽有一时风景好,好景不长当奈何!
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
少时健壮性刚烈,持剑只身去远游。
谁言行游近?张掖至幽州。
谁讲此行游不远?我从张掖到幽州。
饥食首阳薇,渴饮易水流。
饥食野菜学夷叔,口渴便喝易水流。
不见相知人,惟见古时丘。
不见心中知音者,但见古时荒墓丘。
路边两高坟,伯牙与庄周。
路边两座高坟墓,乃葬伯牙与庄周。
此士难再得,吾行欲何求!
贤士知音难再得,远游还想何所求?
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
种植桑树在江边,指望三年叶可采。
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
枝叶长出将茂盛,忽然遇到山河改。
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
树枝树叶被摧折,树干树根浮大海。
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!
春蚕无叶不得食,无茧寒衣哪里来?
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。
不把根植在高原,如今后悔亦无奈!
参考资料:
1、
郭维森 包景诚.陶渊明集全译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6:187-200荣荣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。
荣荣:繁盛的样子。这两句写当初分别之景,有起兴的作用。兰取其贞洁,柳取其惜别。
初与君别时,不谓行当久。
君:指出门的游子。不谓行当久:没说此行要很久。
出门万里客,中道逢嘉(jiā)友。
中道:中途。嘉友:好友。
未言心相醉,不在接杯酒。
心相醉:内心已为之倾倒,即一见倾心。这两句是说,尚未饮酒交谈,便一见倾心。
兰枯柳亦衰,遂令此言负。
言:指临别誓约。负:违背,背弃。
多谢诸(zhū)少年,相知不忠厚。
多谢:多多告诫。相知不忠厚:当面相知的朋友未必就是忠厚之人。
意气倾人命,离隔复何有?
意气:情谊,恩义。倾人命:送性命。离隔:分离,离弃。
辞家夙(sù)严驾,当往至无终。
夙:早晨。严驾:整治车马,准备出行。志无终:向往到无终去。志:一作“至”,亦通。无终:古县名,在今河北省蓟县。
问君今何行?非商复非戎。
今何行:现在到那里去做什么。商:经商,做买卖。戎:从军。
闻有田子泰,节义为士雄。
田子泰:即田畴,字子泰,东汉无终人。田畴以重节义而闻名。节义:气节信义。士雄:人中豪杰。士,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。
斯人久已死,乡里习其风。
斯人:此人,指田畴。习其风:谓继承了他重节义的遗风。
生有高世名,既没传无穷。
生:生前,在世时。高世名:在世上声誉很高。既没:已死之后。
不学狂驰子,直在百年中。
狂驰子:指为争名逐利而疯狂奔走的人。直:只,仅。百年中:泛指人活一世的时间。
仲春遘(gòu)时雨,始雷发东隅(yú)。
仲春:阴历二月,遘:遇,逢。东隅:东方。古人以东方为春。
众蛰(zhé)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
众蛰:各种冬眠的动物。蛰,动物冬眠。潜骇:在潜藏处被惊醒。从横舒:形容草木开始向高处和远处自由舒展地生长。从:同“纵”。以上四句描写季节变化。
翩(piān)翩新来燕,双双入我庐。
翩翩:轻快飞翔的样子。庐:住室。
先巢故尚在,相将还旧居。
先巢:故巢,旧窝。故:仍旧。相将:相随,相偕。旧居:指故巢。
自从分别来,门庭日荒芜;
我心固匪石,君情定何如?
我心固匪石:是说我的心并非石头,是不可转动的。比喻信念坚定,不可动摇。固:牢固,坚定不移。匪:非。君:指燕。
迢(tiáo)迢百尺楼,分明望四荒,
迢迢:本义指遥远的样子,这里形容高高的样子。分明:清楚。四荒:四方荒远之地。
暮作归云宅,朝为飞鸟堂。
归云宅:是说白云晚上把它当作住宅。形容楼之高。飞鸟堂:飞鸟聚集的厅堂。
山河满目中,平原独茫茫。
茫茫:辽阔,深远。
古时功名士,慷慨争此场。
功名土:追逐功名利禄之人。此场:指山河、平原。
一旦百岁後,相与还北邙(máng)。
百岁后:去世以后。相与:共同,同样。北邙:山名,在洛阳城北,东汉、魏,西晋君臣多葬此山。这里泛指墓地。
松柏为人伐,高坟互低昂。
互低昂:形容坟堆高低不齐。昂:高。
颓(tuí)基无遗主,游魂在何方!
颓基:倒塌毁坏了的墓基。遗主:指坟墓的主人,即死者的后代。
荣华诚足贵,亦复可怜伤。
“荣华”两句:是说对于那些生前追求功名的人来说,荣华的确是珍贵的,但死后一无所得,且如此凄凉,也实在可怜可悲。
东方有一士,被服常不完;
被服:所穿的衣服。被,同“披”。不完:不完整,即破烂。
三旬九遇食,十年著(zhuó)一冠。
著:戴。冠:帽子。
辛勤无此比,常有好容颜。
好容颜:愉悦的面容,这里有乐贫之意。
我欲观其人,晨去越河关。
观其人:访问他。越河关:渡河越关。
青松夹路生,白云宿檐端。
“青松”两句:写东方隐士的居处,在青松白云之间,形容高洁。
知我故来意,取琴为我弹。
故来意:特地来的意思。
上弦惊别鹤,下弦操孤鸾(luán)。
上弦、下弦:指前曲、后曲。别鹤:即《别鹤操》,古琴曲名,声悲凄。孤鸾:即《双凤离鸾》,汉琴曲名。
愿留就君住,从令至岁寒。
就君住:到你那里一起住。至岁寒:直到寒冷的冬天,这里是喻坚持晚节。《论语·子罕》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。”
苍苍谷中树,冬夏常如兹;
苍苍:深青色,犹言“青青”。树:指松柏。常如兹:总是这样,谓郁郁葱葱,不凋零。
年年见霜雪,谁谓不知时。
时:季节的变化。暗寓时世。以上四句起兴,以松柏的坚贞自喻。
厌闻世上语,结友到临淄(zī)。
世上语:泛指世俗流言。临淄:地名,战国时齐国国都,在今山东省。
稷(jì)下多谈士,指彼决吾疑。
稷下:古地名,战国齐都临淄城稷门(西边南首门)附近地区。齐宣王招集文学、学术之士在此讲学。谈士:善于言谈论辩之人,指稷下之士。谓这些人善空谈而不耐霜雪的考验。指彼:指望他们。决我疑:解决我的疑问。
装束既有日,已与家人辞。
装束:整备行装。既有日:已经有好几日。
行行停出门,还坐更自思。
“行行”两句,写临行时又徘徊不前,犹豫再三,表示内心复杂矛盾的状态。
不怨道里长,但畏人我欺。
道里:道路里程,即路程。人我欺:即人欺我。人,指“谈士”。
万一不合意,永为世笑嗤(chī)。
不合意:见解不同。嗤:讥笑。逯本作“之”,今从焦本改。
伊怀难具道,为君作此诗。
伊:此。难具道:难以详细他讲出来。君:泛指读者。
日暮天无云,春风扇微和。
扇:用作动词,吹动。扇微和:春风吹拂,天气微暖。
佳人美清夜,达曙(shǔ)酣(hān)且歌。
佳人:美人。美清夜:爱清夜。达曙:到天明。酣:酒足气振的样子。
歌竟长叹息,持此感人多。
歌竟:歌唱完了。此:指下文四句歌辞。持此:仗着这支歌曲。感人多:十分动人。
皎皎云间月,灼灼叶中华。
皎皎:光明的样子。灼灼:花盛的样子。华:同花。
岂无一时好,不久当如何。
一时好:一时之美好。指“云间月”圆而又缺,“叶中花”开而复凋。
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
厉:性情刚烈。
谁言行游近?张掖(yè)至幽州。
张掖:地名。
饥食首阳薇,渴饮易水流。
易水:水名。
不见相知人,惟见古时丘。
丘:坟墓。
路边两高坟,伯牙与庄周。
伯牙:古代音乐家。庄周:庄子。
此士难再得,吾行欲何求!
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
“三年”句是说盼望三年之内可以采桑养蚕。
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
始:才。值:逢。
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
柯:枝干。沧海:指东海。这两句是说桑树的枝干被摧折了,根叶漂浮到大海中去了。
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!
欲谁待:即欲何待,还依靠什么?
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。
本:桑树枝干。这两句是说桑树不种在高原上,而种在江边,根基不巩固,所以摧折,有什么可后悔的?
参考资料:
1、
郭维森 包景诚.陶渊明集全译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6:187-200荣荣窗下兰,密密堂前柳。
初与君别时,不前行当久。
出门万里客,中道逢嘉友。
未言心相醉,不在接杯酒。
兰枯柳亦衰,遂令此言负。
多谢诸少年,相知不忠厚。
意气倾人命,离隔复何有?
辞家夙严驾,当往至无终。
问君今何行?非商复非戎。
闻有田子泰,节义为士雄。
斯人久已死,乡里习其风。
生有高世名,既没传无穷。
不学狂驰子,直在百年中。
仲春遘时雨,始雷发东隅。
众蛰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
翩翩新来燕,双双入我庐。
先巢故尚在,相将还旧居。
自从分别来,门庭日荒芜;
我心固匪石,君情定何如?
迢迢百尺楼,分明望四荒,
暮作归云宅,朝为飞鸟堂。
山河满目中,平原独茫茫。
古时功名士,慷慨争此场。
一旦百岁後,相与还北邙。
松柏为人伐,高坟互低昂。
颓基无遗主,游魂在何方!
荣华诚足贵,亦复可怜伤。
东方有一士,被服常不完;
三旬九遇食,十年著一冠。
辛勤无此比,常有好容颜。
我欲观其人,晨去越河关。
青松夹路生,白云宿檐端。
知我故来意,取琴为我弹。
上弦惊别鹤,下弦操孤鸾。
愿留就君住,从令至岁寒。
苍苍谷中树,冬夏常如兹;
年年见霜雪,谁前不知时。
厌闻世上语,结友到临淄。
稷下多谈士,指彼决吾疑。
装束既有日,已与家人辞。
行行停出门,还坐更自思。
不怨道里长,但畏人我欺。
万一不合意,永为世笑嗤。
伊怀难具道,为君作此诗。
日暮天无云,春风扇微和。
佳人美清夜,达曙酣且歌。
歌竟长叹息,持此感人多。
皎皎云间月,灼灼叶中华。
岂无一时好,不久当如何。
少时壮且厉,抚剑独行游。
谁言行游近?张掖至幽州。
饥食首阳薇,渴饮易水流。
不见相知人,惟见古时丘。
路边两高坟,伯牙与庄周。
此士难再得,吾行欲何求!
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
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
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
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!
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。
拟古,就是摹拟古诗之意。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,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。从内容来看,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、寄托感慨之作,其中多有托古讽今、隐晦曲折之辞。
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,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,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,违背誓约,轻易初心。
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,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,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、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。
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,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,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。
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。江山满目,茫茫无限,历史沧桑,古今之变,尤显人生一世,何其短暂!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,早已身死魂灭,只剩下荒坟一片,实在可怜可伤。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、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。
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,实则是诗人自咏,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。
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,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。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,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,不受世俗之欺,所以写诗以明志。
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,感叹欢娱夜短、韶华易逝的悲哀,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。
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,壮年时期的情怀,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。
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,晋恭帝为刘裕所立,犹如“种桑长江边”。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,根基不牢自取灭亡。“今日复何悔”,诗人痛惜之情可见。
总体而言,陶渊明的《拟古九首》写的都是在朝代、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。全诗感情低回缠绵,语言曲折宛转。这几首诗题为“拟古”,从中可看到《古诗十九首》、汉乐府、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,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、第二首的一问一答、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,以及轻浅的词语、叠词等等。之所以用拟古作题,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,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,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参考资料:
1、
郭维森 包景诚.陶渊明集全译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6:187-2002、
陈庆元等 编选.陶渊明集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4:174-185
向上折叠
展开剩余(

)
 )
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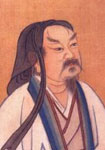
 120篇诗文
120篇诗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