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,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,皆为惠连;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,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?如诗不成,罚依金谷酒数。(桃花 一作:桃李)
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,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,皆为惠连;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,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?如诗不成,罚依金谷酒数。(桃花 一作:桃李)
天地是万物的客舍,时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。死生的差异,就好像梦与醒的不同,纷纭变换,不可究诘,得到的欢乐,又能有多少呢?古人夜间执着火炬游玩,实在是有道理啊。况且温和的春天以秀美的景色来招引我们,大自然又给我们展现锦绣风光。相聚在桃花飘香的花园中,畅叙兄弟间快乐的往事。弟弟们英俊优秀,个个都有谢惠连那样的才情,而我作诗吟咏,却惭愧不如谢灵运。清雅的赏玩不曾停止,高谈阔论又转向清言雅语。摆开筵席来坐赏名花,快速地传递着酒杯醉倒在月光中。没有好诗,怎能抒发高雅的情怀?倘若有人作诗不成,就要按照当年石崇在金谷园宴客赋诗的先例,谁咏不出诗来,罚酒三杯。
参考资料:
1、
吴楚材 吴调侯.古文观止:中华书局,1959年9月2、
刘海波主编;宋少兵编写.初中生经典诵读 九年级上册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07:第123-125页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,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,皆为惠连;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,高谈转清。开琼
(qióng)筵
(yán)以坐花,飞羽觞
(shāng)而醉月。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?如诗不成,罚依金谷酒数。(桃花 一作:桃李)
逆旅:客舍。逆:迎接。旅:客。 迎 客止歇,所以客舍称逆旅。过客:过往的客人。浮生若梦:意思是,死生之差异,就好像梦与醒之不同,纷纭变化,不可究诘。秉烛夜游:谓及时行乐。秉:执。有以:有原因。这里是说人生有限,应夜以继日的游乐。秉,执。以,因由,道理。阳春:和煦的春光。召:召唤,引申为吸引。烟景:春天气候温润,景色似含烟雾。大块:大地。大自然。假:借,这里是提供、赐予的意思。文章:这里指绚丽的文采。古代以青与赤相配合为文,赤与白相配合为章。序:通“叙”,叙说。天伦:指父子、兄弟等亲属关系。这里专指兄弟。群季:诸弟。兄弟长幼之序,曰伯(孟)、仲、叔、季,故以季代称弟。季:年少者的称呼。这里泛指弟弟。惠连:谢惠连,南朝诗人,早慧。这里以惠连来称赞诸弟的文才。咏歌:吟诗。康乐:南朝刘宋时山水诗人谢灵运,袭封康乐公,世称谢康乐。琼筵:华美的宴席。坐花:坐在花丛中。羽觞:古代一种酒器,作鸟雀状,有头尾羽翼。醉月:醉倒在月光下。金谷酒数:金谷,园名,晋石崇于金谷涧(在今河南洛阳西北)中所筑,他常在这里宴请宾客。后泛指宴会上罚酒三杯的常例。
参考资料:
1、
吴楚材 吴调侯.古文观止:中华书局,1959年9月2、
刘海波主编;宋少兵编写.初中生经典诵读 九年级上册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07:第123-125页 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,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,皆为惠连;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,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?如诗不成,罚依金谷酒数。(桃花 一作:桃李)
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、饮酒赋诗的情景。作者感叹天地广大,光阴易逝,人生短暂,欢乐甚少,而且还以古人“秉烛夜游”加以佐证,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,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。文章写得潇洒自然,音调铿锵,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。
本文开笔气势夺人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”
作者感叹天地广大,无穷无尽,光阴易逝,人生短暂,欢乐甚少。而且还以古人“秉烛夜游”加以佐证。文章开头从对天地、光阴的思考起笔,发出对天地、万物、人生的感喟,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,表达出他潇洒出尘,超凡脱俗的风度。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、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,并要大家享受自然、享受生命,及时行乐。
“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假我以文章”,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“况”承接前面,进一步回答了“为何”。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”,因而应该“夜”宴;更何况这是春季的“夜”,“阳春”用她的“烟景召唤我”,“大块”把她的“文章”献给我,岂容辜负。因而更应该“夜”宴。这两句确实佳妙:第一,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。春天的阳光,暖烘烘,红艳艳,惹人喜爱。“春”前着一“阳”字,就把春天形象化,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,眼前呈现一片红艳。春天地气上升,花、柳、山、水,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,都披绡戴骰,分外迷人。那当然不是绡彀,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。“景”前着一“烟”字,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。此后,“阳春烟景”,就和作者在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中所创造的“烟花三月”一样,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。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“文章”,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、赏心悦目的感受。第二,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。那“阳春”是有情的,她用美丽的“烟景”召唤我;那“大块”也是有情的,她把编烂的“文章”献给我。既然如此,作为审美主体的”我”自然主客拥抱,融合无间了。
“会桃李之芳园”以下是全文的主体,兼包六个要素,而着重写“如何”。“会桃李之芳园”,不是为了钱别,而是为了“叙天伦之乐事”。这一句,既与“为欢几何”里的“欢”字相照应,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。这是“叙天伦之乐事”的“欢”。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,作为封建社会里的“浮生”,难得享天伦之乐。如今,不但相会了,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李园中,阳春既召我以烟景,大块又假我以文章,此时此地,“叙天伦之乐事”,真是百倍的欢乐。
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,撞书画,作者便说“群季诸弟俊秀,皆为惠连”。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,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。“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”,不过是自谦罢了。人物如此俊秀,谈吐自然不凡。接下去的“密赏未已,高谈转清”,虽似双线并行,实则前宾后主。贯”的对象,就是前面所写的“阳春烟景”“大块文章”和“桃李芳园”;“谈”的内容,主要是“天伦乐事”,但也可以包括“赏”的对象。“赏”的对象那么优美,所以贫”是“密赏”;“谈”的内容那么欢乐,所以“谈”是“高谈”。在这里,美景烘托乐事,幽贯助长高谈,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。
“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”两句,集中写“春夜宴桃李园”,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。“月”乃“春夜”之月,“花”乃“桃李”之花。兄弟相会,花月交辉,幽赏高谈,其乐无穷,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。“飞羽觞”一句,李白从“羽”字着想,生动地用了个“飞”字,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,但光痛饮,就不够“雅”。他们都是诗人,痛饮不足以尽兴,就要作诗。于是以“不有佳作,何伸雅怀”等句结束了全篇。
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全文百余字,紧扣题目,字字珠玑,句句溢彩。文章虽短,然跌宕有致,风格清俊潇洒,语言流畅自然。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。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,文中不管是记时、记地、记人、记事,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,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,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,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,充实而欢畅,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。
参考资料:
1、
陈振鹏,章培恒主编.古文鉴赏辞典 上 第1版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4.07:第829-831页2、
曹余章主编.历代文学名篇辞典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0年06月第1版:第338页 )
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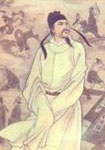
 170篇诗文
170篇诗文